
Photo Credit: Maxpixel
本文獲合作媒體 36kr 授權轉載,Smiletalker 編譯,作者 Michael Harris。 很長一段時間,Michael Harris 確信自己沉浸在書籍中的童年將使他不受新媒體的影響,他可以繼續以原來的方式閱讀,因為他的思想在網路誕生以前就已經形成。然而他錯了。作者認為我們通過電子螢幕閱讀的方式獲取來的訊息量大卻不精,還消磨了我們思考的能力,麻木了我們的閱讀愉悅感,扭曲了我們對時間的認知和感覺。
有一天晚上,我放下手機打開一本書,我給自己定了一次讀完一章的任務。這看上去很簡單,但我卻做不到。我的視力沒有任何問題,沒有中風或其他疾病蒙上了陰影。然而,老實說,做不到也很正常。
段落旋轉、句子像樹枝一樣折斷、思緒逐漸飄遠。這是閱讀的常態。我把我的視線重新拖回書頁上,嘗試專注。半小時後,我扔下書去 Netflix 看劇。
與另一位作家共進晚餐時,我說:「我認為我已經忘記瞭如何閱讀。」
「是的!」他拿著他的刀回答道。「所有人都一樣。」
「不,真的,」我說。「我的意思是我實際上無法閱讀了。」
他點頭道:「沒人能像他們過去那樣閱讀,但沒有人談論這個問題。」
這是很丟臉的事情。特別是對於像我這樣的人。我是一位作家,文字是我的工作。沒有閱讀,就沒有我。所以,意識到這一點令人不安:我忘記瞭如何閱讀,如何真正的閱讀,而且我一直拒絕談論這件事。
書籍曾經是我的避難所。睡前閱讀 Highsmith 的小說是一種習慣。閱讀就是離開現實世界,超脫於緊張的現實。閱讀是為了讓自己快樂,並在此過程中體驗更多。我確實認為傳統的、面向書本的閱讀風格給我打開了一個世界,尤其是在放下書本之後。面向螢幕的新閱讀風格似乎具有相反的效果:打開電子設備之後,就關閉了與世界的連接。
我們正以一種非常真實的方式,失去舊的閱讀風格,也失去自己的一部分。
對於大多數現代生活,正如媒體評論家尼爾波斯特曼所說,印刷品是「所有話語的模型,隱喻和尺度。」與印刷書籍的共鳴,它們的線性結構以及它們對我們注意力的要求,觸及我們繼承的世界的每一個角落。但網路生活使我成為一種不同類型的讀者,我為了一個有用的事實蒐集資料,不久之後,我的注意力又到了其他網站連結上。我的注意力,也就是我的經驗,破裂了。線上閱讀是關於點擊量,評論和點讚。當我採取這種思維方式,並嘗試將其應用於被平裝的書本時,我的頭腦就會消失。
《淺薄》的作者 Nicholas Carr 說:「數位技術讓我們變得「更難以忍受沒有新刺激到來的時光。」所以,我扔掉書籍,渴望得到某種精神辣椒醬。 然而,並非每一種情緒都可以由一種表情符號代替,並不是每一種想法都可以通過發推特傳達出來。
甚至是 Google 的前 CEO 埃里克施密特也對他的企業幫助培養的這種心理景觀感到焦慮。他曾告訴 Charlie Rose:「我擔心我們被打斷的程度,資訊的壓倒性...... 實際上影響著我們的認知,它影響著更深度的思考,我仍然相信坐下來讀書是真正學習一些東西最好的方式,我擔心我們正在失去它。」事實上,現在有大量來自神經科學家報導,如 Susan Greenfield 和 Gary Small 表明,數位世代的大腦的確與前代人不同。每天花 10 個小時盯著螢幕,你的大腦突觸也會隨之改變。
很長一段時間,我相信自己沉浸在書籍中的童年將使我不受新媒體的影響,我可以繼續以舊的方式閱讀和寫作,因為我的思想是在網路誕生以前裡形成的。但大腦是可塑造的,我已經變了。我不再是那個閱讀的人。
當我們成為憤世嫉俗的讀者時,我們以網路生活鼓勵的、脫節的、以目標為導向的方式閱讀時,我們就停止了對注意力的鍛煉。我們不再閱讀書籍,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的閱讀會減少,完全沒有。事實上,我們生活在一個文字大雜燴的社會中, 關鍵在於我們是否真正閱讀,我們如何閱讀。這就是我們每個人都需要自己判斷的事情;統計局無法統計。
對於我自己來說:我知道我的閱讀量不會減少,但我也知道我讀得很糟糕。
技術一直在扭曲我們的時間感。教堂的鐘聲把一天分成幾段。工廠鳴哨迎來工人一天的開始。但目前的手機訊息聲讓我們比以往更加扭曲。我們不僅期望被打斷,而且還主動要求它。早在 1890 年,William James 在《心理學原理》中寫道:「我們的時間感似乎受制於對比律。」
馬歇爾麥克盧漢認為,每種技術「在第一次內化期間都有能力麻痺人類的認識」。我們似乎已經消化了我們的設備,他們現在可以麻痺我們享受耐心的樂趣。他們可以讓我們對那種較古老的文字體驗的享受感到麻木。
有一天,我和我蹣跚學步的小侄女呆在一起,而她在她的 iPad 上一邊觀看影片,一邊瀏覽影片播放列表,我把她正在看的影片打開為全螢幕。
我以為我在幫她,但這讓我的侄女陷入恐慌。「小電視!」她堅持說。「不要大電視!」她需要小螢幕,以便觀察接下來的影片列表,在單個影片上聚焦即使是一分鐘也不行。
這個意味著,只需要幾代人時間,我們對媒體的經驗將會被重塑,我們不應該感到驚訝。相反,那時我們會對我們曾經讀書這一事實感到驚訝。Maryanne Wolf 和 Alison Gopnik 等傑出的研究人員提醒我們,人類的大腦視覺皮層從來不是為了閱讀而設計。一本小說所要求的深度閱讀並不容易,而且從來不是一件「自然」的事情。
我們的預設狀態是分心。目光轉移,注意力不集中,在環境中尋找線索。(否則,那些在暗處的捕食者可能會吃掉我們。)我們的注意力分散了嗎?一項著名的研究發現人類寧願給自己電擊,而不願獨自思考 10 分鐘。每當我們迷失在書中,我們都會違背這些本能。
自 19 世紀以來,讀寫能力才開始普及。我們的閱讀習慣很容易過時。作家 Clay Shirky 甚至表明,我們最近已經「空洞地稱讚」托爾斯泰和普魯斯特。那些與文學有關的古老而孤獨的經歷「僅僅是生活在貧困通道環境中的副作用」。在網路世界中,我們可以繼續前進。而我們的大腦,只是被書籍暫時劫持,現在將被新事物劫持。
維克多·雨果曾經寫道,書籍取代了建築,它是人類完全革新的表現方式。假設我們的「偉大的筆跡」將在明天被其他手段所取代,這合理嗎?為什麼會這樣?
我們必須注意的是,演算法是多麼有效率和無情。「一本書,」一位作者告訴我說,「實際上只是一個反向工程的 TED 演講,不是嗎?它是一個可以讓你做巡迴演講的平台。」
對於許多作家來說,這是新的智慧。現實的閱讀風格讓位於現實的寫作風格。我看著我自己的書變得「有用」,因為這樣才能進入公眾視野。我從來沒有認為我的書是有用的,尤其是在自我幫助的層面,但這往往是讀者閱讀的目的。我這樣說並不令人吃驚:幾乎每一位採訪者都會問我實際的生活建議,儘管我的書中並沒有提供。
同時,我承認:我現在寫的文字使用了一套新的標準進行篩選。讀者理解了嗎?他們會憤怒嗎?閱讀有障礙嗎?這些句子足夠簡短嗎?想法足夠簡單嗎?讓自己變成一個現實的作家是很誘人的,因為我已經是一個現實的讀者。
在矽谷,他們有一種說法解釋了演算法帶來人們不想要的結果的原因:無用輸入,無用輸出。這個想法是說算法只能處理你提供的資訊。作家和所有創作者不都是這樣運算的嗎?我們的工作是處理我們所消耗的東西。輸入美感,輸出美感。輸入垃圾,輸出垃圾。
所以,也許變成一個現實的作家可以進行預防,如果我可以先糾正我的閱讀習慣,記住我曾經閱讀的方式。不掃 QRcode,不分享推特,不摘錄,只閱讀。耐心地、慢慢地、無用地閱讀。
從某種意義上說,書籍一直是時間機器。如今,書籍作為時間機器的能力更加明顯,甚至更具啟發性。它們可以將我們帶回到網路以前的精神框架。那些孤獨的旅程對於孤獨的當代人來說更具豐富性。
原文鏈接:https://www.theglobeandmail.com/opinion/i-have-forgotten-how-toread/article37921379/
from INSIDE 硬塞的網路趨勢觀察 http://ift.tt/2FeKr0M
 Photo credit: Sergey Galyonkin
Photo credit: Sergey Galyonkin 



 Photo Credit:Google
Photo Credit:Google  Photo Credit:Google
Photo Credit:Google  REUTERS/Jonathan Ernst
REUTERS/Jonathan Ernst  Photo Credit:OFFICIAL LEWEB PHOTOS
Photo Credit:OFFICIAL LEWEB PHOTOS  REUTERS/Benoit Tessier
REUTERS/Benoit Tessier 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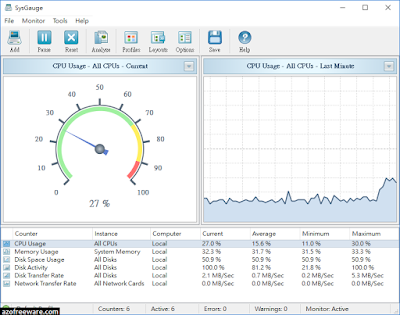

 Photo Credit: Maxpixel
Photo Credit: Maxpixel 
 Photo Credit: Inventwood
Photo Credit: Inventwood 
 Photo credit: 世界公民文化中心提供
Photo credit: 世界公民文化中心提供  Movavi Video Editor,30分鐘快速製作優質影片! 軟體名稱:Movavi Video Editor 免費下載:
Movavi Video Editor,30分鐘快速製作優質影片! 軟體名稱:Movavi Video Editor 免費下載:

 步驟二:裁剪多餘影像 ▼ 要去除影片中多餘的畫面,只要使用「剪刀圖示」的功能,就可以非常快速的刪除不要的片段哦。
步驟二:裁剪多餘影像 ▼ 要去除影片中多餘的畫面,只要使用「剪刀圖示」的功能,就可以非常快速的刪除不要的片段哦。 步驟三:加入影片濾鏡 ▼ 影片濾鏡有相當多種,使用者可以挑選自己喜愛的樣式套用即可。
步驟三:加入影片濾鏡 ▼ 影片濾鏡有相當多種,使用者可以挑選自己喜愛的樣式套用即可。
 步驟四:加入轉場效果 ▼ 轉場效果素材相當充足,分類上也可以讓使用者直接點選並且預覽轉場效果。
步驟四:加入轉場效果 ▼ 轉場效果素材相當充足,分類上也可以讓使用者直接點選並且預覽轉場效果。
 步驟五:加入文字標題 ▼ 文字標題內建相當多範例可以套用,只要將文字範例拖曳在影片上方,就可以馬上看到效果,並且可以在右上角的小視窗中預覽哦。
步驟五:加入文字標題 ▼ 文字標題內建相當多範例可以套用,只要將文字範例拖曳在影片上方,就可以馬上看到效果,並且可以在右上角的小視窗中預覽哦。 步驟六:加入背景音樂 ▼ 一段影片最重要的就是背景音樂,要挑選好音樂才能讓影片更有表達的情境在裡面哦。
步驟六:加入背景音樂 ▼ 一段影片最重要的就是背景音樂,要挑選好音樂才能讓影片更有表達的情境在裡面哦。
 步驟七:完成影片 ▼ 經過以上步驟反覆添加影片,小編專注的花了30分鐘編輯這段5分鐘的影片就完成了。
步驟七:完成影片 ▼ 經過以上步驟反覆添加影片,小編專注的花了30分鐘編輯這段5分鐘的影片就完成了。
 Movavi Video Editor影片作品 [embedded content] 更多關於 Movavi 產品文章
Movavi Video Editor影片作品 [embedded content] 更多關於 Movavi 產品文章